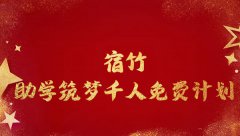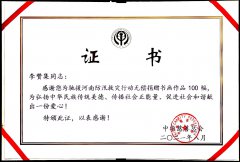今日乡村,更多赖于现代人之于自然田园的某种幻觉,还是赖于城乡供给当中,人之于生活的基础需求?作为情动之地,乡村或幸存于所谓乡愁、乡恋的审美话语,或重构于相对比较封闭和保守的底层话语,或收编于城市发展的权力话语,再或者,混同于网络视频的残酷话语……
仅仅一个世纪,现代性早已大获全胜,传统的乡村连同自然、乡土社会及其人情世故,似乎很轻易就烟消云散了。
——节选自“谷神变”展览前言
第 11 届上海双年展城市项目
寻乌调查中“反对本本主义”、“走到实际中去发现新问题、提出办法”是我们本次赤燃寻夏大学生三下乡团队进行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。带着发现问题的眼光重新走入家乡的乡镇、田野、果园,走向努力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人。我们把握那些灵动而微妙的现实,试图找到“历史”“现在”“未来”的隐秘线索。
21世纪的中国被灾难、成就、发展截成不同的段落,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迅速变迁。寻乌这座小城,是中国的缩影,寻乌人顽强地在迭代与变动中努力地寻找平衡,古老中国的很多特性在他们身上存在,他们勤劳、忍耐、富有韧性、随遇而安。

(田阿姨在地里)
当我们进行访谈时,田阿姨刚从园子里回来。她匆匆忙忙地踱到水龙头边洗掉手上的灰土,把手上的水渍在裤子上蹭蹭,便忙着张罗切水果倒水来招待我们。“干这行有......快三四十年了吧,打小就跟着家里人种,干了一辈子,踏实。我们寻乌的柑橘类作物是很多的,冬天有脐橙,夏天卖夏橙,秋天了蜜桔熟了也得忙。每家每户就是得忙一整年的,闷头扎进土里,跟草啊树啊打交道。”说到这里,她又羞怯地咧开嘴笑了。
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是矛盾的,他们一边深沉地爱着脚下的每一捧泥土,感激着其中孕育出的生命、财富与甜美的果实,一边咬牙扛着面对被土地绑定的命运。
生活从来不会是一潭死水,只要是汪洋,便会有风浪。田阿姨的丈夫唐伯告诉我们:“前几年黄龙病这个病啊闹得凶,全县近八成的果山荒废了,完全没办法种,黄龙病传染性是很强的。”
在风浪面前,有人扛不住,割舍掉了故土的疼痛:“家家户户靠橙子养家糊口的,我们小老百姓哪经得起这种折腾。那几年大家可以说基本没收成,很多人下广东找出路了。”但也有人坚持着、坚信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必然不会将他辜负。“我当时没走。家里有两个孩子有老人,老婆一个人照顾不过来。你想,哪些事业发展不遭遇点磨难?我们客家人,祖辈训话要吃苦耐劳、不能忘本。啥是本,你说啥是本?这个土就是我们的根。吃这里的水长大的,外边的人都说寻乌灵秀,这个地得有人守。”
我想,寻乌的马蹄河始终滔滔不绝,流淌在寻乌人的血液里,构成农民和土地之间始终存在着的某种坚实的、无形的纽带。这纽带来源于客家踏实本分的烙印,来源于骨子里的朴实,来源于沿着漫长岁月跨越而来的深情。而正如播种与耕作必会有收获,唐伯挥舞着手告诉我们,语气中满溢着骄傲:
“这几年好起来了,政策支持搭了防虫网。电商、营销全都搞起来咯!日子一天比一天强,我们现在生活过得好,那真是离不开政府的努力。”

(收获中的寻乌乡民)
“我一干农活的能有啥梦想。就是希望家里的两个女娃别和我们一样,她们念了书的得挣个好前途。这几年做那个电商啊卖脐橙,听说好像还不错,物流那块,轻松、收入高,做电商之类的她们比我懂。反正就,最好别跑太远,别忘本。”
“最后悔的就是没念啥书,没文化嘛,土呗。我这也就是和你聊聊天那样的哦,没文化说不出什么有文采的来,不比你们大学生。合照就不拍了,我太土了,没啥气质,就是个种果子的。”

(钓鱼的寻乌乡民)
“土”这个字里包含着一个巨大的世界,折射着农民作为一个人的生活结构。在这样一个后现代思潮涌起的社会中,许多人不断地解构“土”并赋予新的含义,想改造这个看起来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词。我们尝试走入乡村现场,触摸最真实的经验,看到了农民曾经的辛酸、犹豫、喜悦,看到他们如何用力地生活。当我们看到农民在打击中摸索求生、看到他背后的家庭,我们就意识到他不该被“土”这个符号定义。
当我们聊到在种植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时,周伯伯大倒苦水:黄龙病带来的大肆减产,果树死伤大片;今年疫情期间运输行业大批停运,导致一箱箱的脐橙滞销,资金无法回笼...可是我们问起有没有想过转行时,他却坚定地摇了摇头。“我啊,也就会和果子打交道啦,种得舒心,种得踏实。”
我们希望将“土”清洗出更具原真的意义,看到了“踏实”。无论多么困难,这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仍然用力地生活,我们觉得辛酸但又感到温暖、有力量。千百年来,这种从土里生长出的朴素情感慢慢成为民族灵魂的压舱石。
城镇化年代,如何理解乡村?唯有踏入真实的乡村现场,打破城市的暴力凝视、浪漫化凝视,我们才能真正地看到其最本真的生长形态。这也正是我们初入学术门槛的学生在努力靠近的——掏空自己,汲取滚动在社会事实中的营养,敲碎“土气”的刻板标签,睁大眼睛,从茧壳中跳出来。
撰稿人: 谢 婕、葛婉宁
访谈对象:田阿姨、唐伯伯、周伯伯
审稿人:张建锋